书法也像人一样,有筋、有骨、有血、有肉,此四者缺一都是书病。包氏《艺舟双辑》说:筋者锋之所为,骨者毫之所为,血者水之所为,肉者墨之所为,锋为笔之精,水为墨之髓。锋能将副毫,则水受摄,副毫不裹锋,则墨受运。又说:字有骨肉筋血,以气充之,精神乃出,不按则血不溶,不提则筋不劲,不平则肉不匀,不颇则骨不骏。圆则提按,出以平颇,是为绞转;方则平颇,出以提按,是为翻转,知绞翻则墨自不枯,而毫自不裹矣。此使转之真诠,古人之秘密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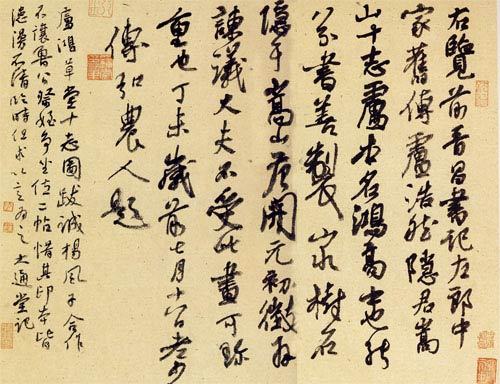
读了包氏的书,可以明白书的筋、骨、血、肉的区别、由来,就可以做到筋、骨、血、肉俱备。后人未深究此事,致使不少名家也犯此病,所以不妨一提。包氏说:“以气充之,精神乃出。”是四者之来,也在笔力的基础上,笔没有力,就不能把四者搞好。笔画没有力,则书没有精神,没有“生气”,“生气”也就是“以气充之”的“气”。所以古人的“全身力到”、“笔力惊绝”就是一个基本的功夫了。李斯的“下笔如鹰隼攫”,钟繇的“点若山颓”,王羲之的“点画波撇屈曲,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”,以至王宗炎《论书法》的“通身精神赴之”,蒋骥《续书法论》的“作书用全力,笔画如刻,结构如铸”,包世臣的“知点画细如丝发,皆须全身力到”,都可以说是书法上的基本问题。未能用全副精神去抓笔、运笔,就无法使字有“生气”,则一切都谈不上了。
筋是锋的作用,笔没有力,从纸面上滑过去,就谈不上肉里的筋。锋要正,用中锋,乃能发挥锋的力量,运笔要逆入涩进,才能用得着中锋。偏锋斜扫过去,是不会“力透纸背”的。笔锋不能发生作用,则筋无从生,肉肥的且成为墨猪。笔毫的外层为副毫,副毫不受裹而“万毫齐辅”,则骨刚健,才能发挥气的作用。指运者易裹其锋,不能使“万毫齐力”,字就不可能有骨,字而无骨,怎能站起来呢?笔笔卧在纸上,还能成字吗?血既为水的作用,则用墨不可枯干,枯干则没有血了,也没有肉了。作书干润并用,以求变化,本是好事,但多用干笔则血少,所以要血华,必须用丰润之笔,浓墨湿笔,血肉都好,若笔画瘦而干,则两者都不足道了。淡墨也有问题,太淡则肉也不会丰,墨要得宜,血肉才能秀润。但用墨太浓,腕力弱者就难于运用,赵宋而后,运指者多,所以能榜书者就罕见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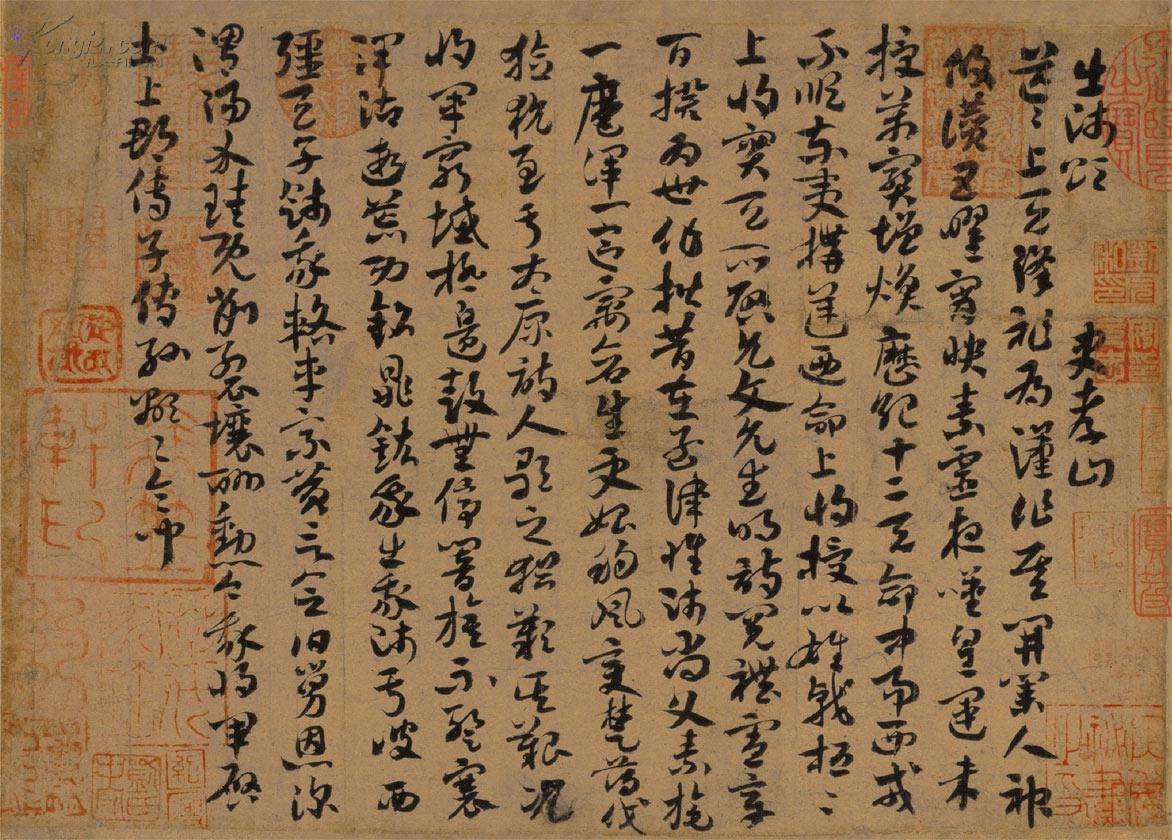
总之,第一要锻炼腕力,“全身力到”,则一切毛病都能消减。因为毛是软的,又是滑的,用这种工具,而要求写出铁画银钩的字,矛盾实在太大了,要用尽一切方法去解决此矛盾,所以由书法进而为书学,其著述也就“汗牛充栋”了。因为问题不少,有时顾了东又顾不了西。像上面包氏的提法,不用笔向下按,血就不融和;不用笔向上提,筋就不劲;笔毫不平辅,肉就不均匀;笔不用侧势——逆势入纸,就不劲骏——严整。圆笔用提而下按,出以平侧乃是绞转;方笔用平侧,出以提按,乃是翻转,懂得绞和翻的笔法,墨就能入纸而不枯干,而笔毫也不会被裹了。但问题还不止此,唐太宗李世民说:缓则滞而无筋,急则病而无骨,横毫侧管,则钝漫而多肉,竖笔直锋,则干枯而露骨。及其悟也,思与神合,同乎自然。
这里是说,写字不能太慢,又不能太快,两者都会出毛病。侧管而用偏,就会迟滞而肥,正锋运笔,又使墨不易下而枯干露骨。这些毛病,在熟练之后自能领悟而克服的。蔡邕说:“笔惟软则奇怪生焉。”笔毫越软就越能变化,越生动,字也越高妙。但越软就越难操纵,所以问题就越复杂了。

马以筋多肉少者为上,字也一样,不能肉多于筋。但要筋骨血肉四者都好,则字肥容易做到;然肥瘦二体,则瘦比肥容易得多。苏东坡说,江南李国主不为瘦硬便不成字。因为肥字要腕力强,瘦的容易应付,所以李国主就不敢作肥字了。瘦字也难于筋骨血肉都好,像汉《冯君阙》,笔画那么细,而又那么雄厚,四者都具备,真是难于下笔的。所以写字,应于肥上下功夫,使四者都好,能运腕力全身力到的,也非难事。而“全身力到”,也成为不磨之论了。学书者不能不于此下苦功,争取做到“笔力惊绝”,才是正途。
本网编辑:项硕











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